朱光亚 把血汗洒在祖国的大地上
来源:《科学家精神·爱国篇》 日期:2020-05-29
朱光亚(1924年12月—2011年2月),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负责并组织领导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究、设计、制造与试验工作,参与领导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制订与实施、国防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组织领导了禁核试条件下中国核武器技术持续发展研究、军备控制研究及我军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研究等工作,为中国核科技事业和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入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1970—1979年英雄模范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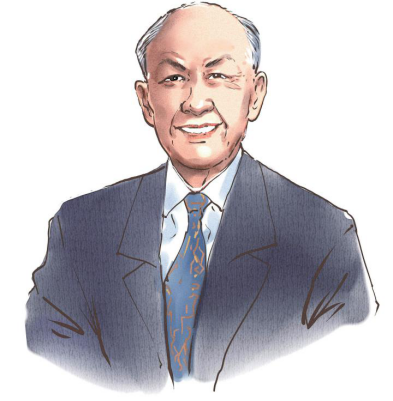
这位传奇科学家平时为人低调,很少抛头露面,创下的功勋却令人为之震惊。半个世纪以来,他始终处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科技决策的高层。在核武器技术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凝聚了他的智慧和决心。无论是发展方向的抉择和决策,还是核武器研制和核试验关键技术问题的决策,他都起到了主导作用,为中国特色核武器事业的持续快速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中国人要做出原子弹,只能靠自己”
抗战胜利后不久,重庆国民政府邀请数学教授华罗庚、物理学教授吴大猷、化学教授曾昭抡赴重庆商讨发展原子武器事宜。3位教授拟订了计划,遴选优秀青年学者赴美考察。朱光亚被吴大猷选中。
1946年8月,朱光亚和李政道、唐敖庆等一起,随同华罗庚从上海乘船赴美。
然而,心怀原子弹之梦的朱光亚等人刚到美国,就碰了个大钉子。先期到达的曾昭抡告诉他们,美国有关原子弹的各个科研机构均不准许外国人进入。刹那间,美梦化为泡影。
残酷的现实使朱光亚醒悟:美国任何时候也不会帮助中国发展尖端科学技术。中国人要做出原子弹,只能靠自己。
师生们考察的热望破灭后,他们决定自谋出路,分别进入美国的研究机构或大学,学习研究前沿科学技术。朱光亚不改初衷,1946年9月,他随吴大猷进入密歇根大学,从事核物理学的学习和研究。在这里,他一边作为吴大猷的助手做理论和计算研究,一边在研究生院学习核物理实验技术,攻读博士学位。
经过不懈努力,朱光亚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的学习成绩始终全部是A,连续4年获奖学金。1947—1949年,他连续在《物理评论》上发表了4篇论文,在发展迅速的核物理领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1949年6月,25岁的朱光亚完成了博士论文,顺利通过论文答辩,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
“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1950年年初,朱光亚牵头起草的《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中这样写道。
当时密歇根大学的中国学子十分关注国内形势,作为中国学生的学生会主席,朱光亚常组织大家围坐在草坪上传阅《华侨日报》,宣读家信,传递国内消息。
“只有把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聪明才智献给祖国,个人的人生价值和理想才能实现。”朱光亚认为。因而,他积极地向大家宣传国内形势,激励大家的爱国情怀,呼唤同学们努力学好科学知识报效国家。1950年2月,他拒绝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的旅费,取道香港回国。途中,他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发出了《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
这封公开信登在《留美学生通讯》1950年3月18日第三卷第八期上,在当时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它像一个号召令,让更多海外学子受到感召,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成为建设新中国的栋梁。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55年,党中央做出发展原子能工业的战略决策。此时已是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物理系教授的朱光亚奉调参与筹建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担负起尽快为我国原子能科学技术事业培养专门人才的重任。次年9月,他调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子物理研究室副主任,在所长钱三强的领导下,带领年轻人从事中子物理和反应堆物理研究。
这段时间,他还参与了苏联援建的核反应堆建设和启动工作,发表了《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的物理参数的测定》等论文。同时研制成功第一座轻水零功率装置,这是我国原子能技术研究的一项基础工程,它的意义重大,为我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此外,他还兼任研究所的学术秘书,表现出不凡的科学造诣和较强的科研组织领导能力,深受钱三强的赞赏。
1959年6月,苏联来信拒绝按协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中共中央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来”。朱光亚被调入核武器研究所,并于次年3月被任命为副所长,担任科学技术方面的总负责人,协助所长李觉、副所长吴际霖开展科研组织领导工作。
当时最大的困难是缺少资料,只有1958年宋任穷、刘杰、钱三强、吴际霖等人在听取苏联专家讲授原子弹教学模型课时,记下的一份支离破碎的提纲式记录。朱光亚按照吴际霖的提议,与邓稼先、李嘉尧一起将这些记录整理成了一份较为完整的参考资料。以此为线索,他组织科研人员一边学习了解基本原理,开展自己的理论研究;一边开展科研实验的准备工作,亲自审定大量的技术任务书。
与此同时,他还协助李觉建立了一套科学的规范化的科研管理程序,帮助科研人员养成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作风和科学求实的精神。后来,周恩来总理在一次重要会议上,特意表扬了朱光亚这种严谨细致的科学精神和工作作风。这种精神和作风在核武器研制队伍中一直延续下来,对我国较高的核试验成功率及核武器技术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1960年8月,苏联政府撤回专家,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走上了完全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根据科研工作的需要,朱光亚向二机部提出调集专家和科技骨干的建议。经中央批准,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等著名科学家奉调担任核武器研究所的技术领导,还选调陈能宽、周光召等一批科技骨干,与早先调来的科学家一起形成了研究工作的核心力量。随后,他又与李觉、吴际霖一起组织调整了研究所的科研机构,全面开展理论物理、爆轰物理、中子物理和放射化学、自动控制等研究探索工作。
1962年,我国原子弹的理论设计、爆轰试验、中子源研制等均取得
了重大进展。然而由于正值3年经济困难时期,国内对原子弹研制项目是否“下马”出现争论。9月,二机部部长刘杰与李觉、吴际霖、朱光亚等,向中央提出了两年内进行我国第一个原子弹装置爆炸试验的“两年规划”。
为进一步分析研究其可行性,朱光亚主持起草了《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该文件是当时中国原子弹研制科技工作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对我国在当时科学、工业基础薄弱的条件下,很快完成第一个原子弹装置的研制起到重要作用。
同时,他还主持起草了《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提出将核爆炸试验分两步走,第一个装置先以地面塔爆方式,然后以空投航弹方式进行的方案,不但提前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间,更是能安排较多的测试项目,用来监视原子弹动作的正常与否,检验设计的正确性。这两份至关重要的文件,被誉为“两个纲领性文件”。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威力为2.3万吨TNT当量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试验结果表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从理论、结构、设计、制造到引爆控制系统、测试技术等均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我国又接连取得核航弹、导弹核武器的成功,仅用两年时间就顺利完成原子弹研制的“三级跳”计划,快速实现了原子弹的武器化;同时,仅用两年零八个月时间实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发展速度是世界主要核大国中最快的。朱光亚作为技术总负责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不能只顾埋头搞武器研究”
1996年7月29日9时,在我国又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后,我国向全世界郑重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暂停核试验。
全面停止核试验前后,朱光亚又多次敏锐指出,核武器技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他亲自指导核武器研究院和核试验基地开展禁试后科研发展方向的研讨论证,经中央批准后,很快启动了禁试后核武器技术的研究发展工作。
“我们不能两眼不看世界风云,只顾埋头搞武器研究。”朱光亚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的工作面越来越宽。在国防科技领域,除继续指导核武器和核试验技术研究发展工作外,他还指导了潜艇核动力、核材料技术的研究发展,指导了国防科技与武器装备发展战略研究、武器装备预先研究、国防关键技术报告制定、国家安全重大基础研究、军备控制技术研究等重大工作,提出了许多战略性、前瞻性和创新性的重要思想和建议,为迎接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挑战,实现我国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的跨越式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按照组织上的安排,他还积极参与了国防高科技向民用转移、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以及“军民结合”发展我国高技术等方面的组织领导工作,特别是在我国核电技术发展、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开发和863计划制定与实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五星红旗上永远有您的风采》,付毅飞,
原载于《科技日报》,2011年2月28日。由文正整理)
